
1974年5月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敦阿都·拉薩访华归国,国人夹道欢迎。时年18岁的我,即将修完高中,夹在学生群的欢迎队伍中,分享着这举国欢腾的喜悦。街头触目所及的大小海报,尽是总理与毛泽东主席相见的握手照。这历史时刻的定格从此成为了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史上的经典镜头。
19年后的夏天(1993年),我以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副议长的身份访华,获得时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秦基伟将军的接待,也掀开了我此后常态化访华的序幕。
那年是我同中国交往频繁的一年。当时有幸代表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全程接待莅访的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对我来说,这固然是一份殊荣,也是个人从政生涯中难忘的一页,可更重要的是,那次的莅访标志着马、中议会外交的起点,同时也为两国的交往史增添新的绚丽篇章。自此以后,多位副委员长相继莅访马来西亚更是络绎不绝,一时无两。
同年,我的访华行程先后涵盖了六朝古都的南京、十里洋场的上海,还有双亲故土的海南文昌。难得的是,在摆脱官务缠身之余,我尚能如愿以偿满足自己多年来仅梦游神州的缺憾。从南京的中山陵、原总统府,到上海的四行仓库和原日租界的鲁迅故居,我亲身感受到的是厚重的历史沉淀。到了海南文昌,熟悉的蕉风椰雨,亲切的方言口语,使我暂时忘怀自己只是个初到贵境的陌生人。回到父母的故里,迎来的是初次见面的兄嫂与侄辈们。在他们七嘴八舌的叙说中,隔阂与腼腆很快就融化在浓郁的亲情中。环顾故里的周遭环境,我直觉得自己或许还能为父母的故里建设尽点心力。
万料不及的是,这份遐思竟会在15年后获得实现。2008年我调任马来西亚联邦交通部部长,职务上的因缘际会,让我有机会为辟建吉隆坡-海口之间的民航航线献上一己之力。首航之日,我率团出发,果不其然少了很多中转折腾。回到故里乡下,眼前豁然一亮,曾几何时,周遭道路全已铺上了沥青。整个村庄宛若披上了新装,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那当儿,它同整个中国一样,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空前的自信。
的确,2008年不单是全华夏民族引以为豪的“京奥”年——北京成功举办奧运会,为奥运史留下精彩光辉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正式崛起的开局之年,担负着前所未有的国际重任。当年美国的次贷危机险些引发全球金融恐慌的经验教训,美方或已淡忘,可中国的及时介入施援却是不容抹煞的事实。
同年,我在本身的政党政治生涯中登上了高峰, 当选为本党的党魁。履新后的出访,我首选中国。2009年春节前,在乍暖还寒的元月里,我率领50多人的党团政商代表团来到了北京。那既是一次再续前缘的友好之旅,同时也是开拓商机的经贸之旅。在夯实党际关系之余,经贸的互动也成为了我当时主政本党的聚焦。
令我不曾预料的是,淡出马来西亚政坛后,中国竟成为我工作对接和研究的对象。先是2016年“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的创建,为的是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这可说是我生涯规划中转轨的起点,一个全新领域有待我去开发。两年后,怀着忐忑探索的心情,我再举步跨入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疆域,创立了一家立足马来西亚,放眼亚太的独立智库——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短短的4年里,不自觉间,它已渐涉深水区,成为了多家中国与周边国家智库对接合作的伙伴。
这期间,在中外纷至沓来、瞬息万变的资讯中,我恍然感悟自己正身处于一个百年未得一遇的新变局。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欧美国家对华的甩锅诿过,到冷战思维与民粹主义的复辟,我看到一个固有的全球治理秩序备受意识形态的绑架,其框架正一步步梦游般步向分崩离析的深渊。
或许此次席卷全球的疫情是块照妖镜,它既照出整个人类文明治理的不堪,同时也让披上画皮的魑魅魍魉无所遁形。在欧美国家坐困疫情、竞相抢夺有限的抗疫物资的时候,中方的驰援送暖,却又是另一种人性光辉的写照。
在这强烈的对照下,西方资本财团控制的媒体舆论近年来连番对华丑化,即便是无所不用其极,也阻挡不了中国公共产品相继面世的势头。中国的和平崛起,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展现了一个泱泱大国对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的庄严承担。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复加“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我感受到中国要力挽狂澜,守护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迫切感。
我虽身处边陲,可我不想在这新旧秩序即将交替之际置身事外,错过这历史的节点。诚然,值此人类生存备受威胁的时刻,全球命运休戚与共,已不再是空泛的理念口号,而是刻不容缓、必须全力以赴打赢的一场攻坚战。当然,这绕不开全球的通力合作,同时更需要集举世之智来重塑国际秩序,才有希望走出一条属于大家的康庄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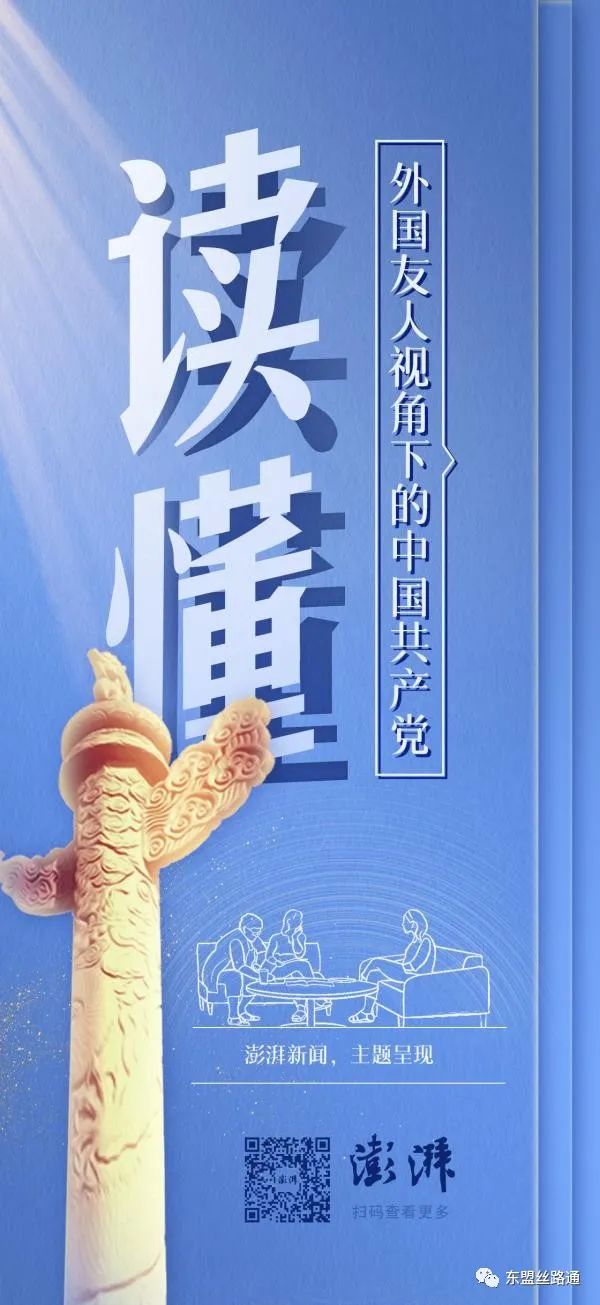
(作者系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原副议长暨联邦交通部原部长)
